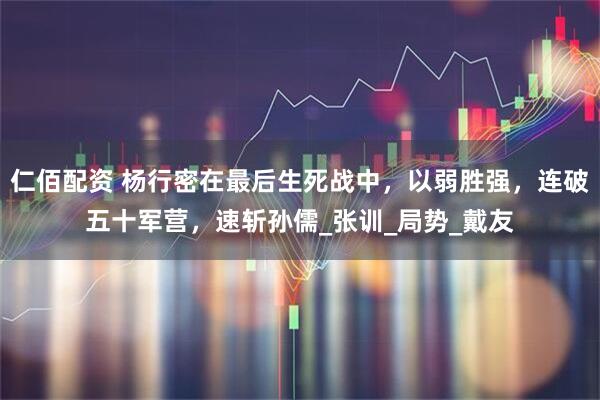
杨行密与孙儒之间的淮南生死对决,始于大顺二年七月,最终在景福元年六月迎来了结局。这场持续三年的历史性战争,深刻影响了十国的命运,牵动了无数人的心。
大顺二年七月,孙儒突然发动了对扬州的火攻,并迅速集结起一支五十万人的大军,决心一举铲除淮南的劲敌杨行密。这一举动迅速激化了双方的冲突,局势骤然紧张。而此时,杨行密的谋士戴友规也迎来了关键时刻。自从杨行密的第一谋臣袁袭去世以来,戴友规一直是他最依赖的重要人物。戴友规曾在关键时刻劝说杨行密坚守宣州,展现了他在杨行密心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。
如今,局势急剧变化,戴友规再次进见杨行密,他不客气地分析形势:“孙儒的兵力不仅众多,而且极为精锐,大部分来自蔡军。蔡军军风凶狠,士兵骁勇,甚至有食人之事发生。相比之下,我军大多是淮人,身材矮小、体力较弱,实力悬殊。若是在平等的条件下与敌交战,我们恐怕难以取胜。更何况,孙儒的兵力远远超过我们,足足是我们的数倍。”说到这里,戴友规的语气愈加沉重,“眼下孙儒已经驻兵在城下,帐篷如林,大敌当前,急需一员能独当一面的将领。”
展开剩余76%杨行密听后心中一震,他明白戴友规所言不虚,局势紧迫,必须做出迅速而果断的决定。于是,他决定重新启用田覠与刘威,尽管两人在之前的战斗中屡次失败,但此刻他们的能力依然至关重要。杨行密深知,如果不及时调整,整个局面恐怕将难以为继。
景福元年,局势终于发生了转机。常州自刘建峰离开后,陈可言占据了该地,而常州对于淮南来说极为关键。这个地方不仅是孙儒、杨行密和钱镠三方争夺的焦点,而且控制了常州,就能掌握南北交通要道。此时孙儒正忙于攻打杨行密,几乎无暇顾及常州的战事。正当局势胶着之际,张训带领大军直奔常州,目标明确,志在必得。
然而,常州的守将陈可言却完全低估了局势,在敌军临近时依然愚昧地选择开门迎战。若他选择弃城而逃,或许还可保全一命,可他在慌乱中与张训交战,最终不敌,一剑丧命。杨行密听闻这一结果后,评价道:“一剑下常州,岂不壮哉!”张训的胜利不仅为整个战局定下了胜算,更为其他将领带来了极大的信心。
紧接着,陶雅接到了杨行密的命令,要誓夺润州这一重要战略地。润州,古称京口,坐落于长江之畔,是浙江的门户,一直是孙儒的重要粮道。虽然陶雅的名声不如李神福响亮,但他却一步步稳扎稳打,最终在杨行密的支持下成功占领了润州,切断了孙儒的关键供应线。
然而,孙儒并未因这次失利而气馁,他依然在宣州指挥着战斗,并试图通过与盟友时溥的合作突破困局。时溥在徐州集结了三万兵力,计划通过楚州进攻扬州,试图稳住孙儒的后方。可惜,时溥的一举一动都在朱全忠的监视下,消息一旦泄露,杨行密便迅速派遣张训和李德诚迎战。寿河之战中,张训与李德诚联合大破时溥军,斩首三千,极大鼓舞了淮南的士气。
时溥的形势愈发艰难,在失去楚州后,他的部下张璲与张谏纷纷投向朱全忠阵营,时溥的支持力量逐渐瓦解,最终在燕子楼自焚而死,留下了一个孤独的结局。
随着战局逐渐倾向杨行密,他的军队在广德频频获胜,孙儒的阵营一个个被击破。而更加不利的局面接踵而至,持续的大雨让孙儒的蔡军遭遇水土不服,瘟疫蔓延,士兵士气低落,粮草短缺。此时,杨行密再次派遣张训,直接切断了孙儒最后的粮道——安吉。
眼看局势更加不利,孙儒决定派遣刘建峰与马殷前往周边州镇寻找粮草,但始终未能获得应有的支持。孤立无援的孙儒,内心充满了不安,预感到大劫将至。此时,淮南军队如同顽强的生物,凭借着几乎没有希望的局面逐渐扭转战局,蚕食孙儒的实力。
当孙儒曾经的骄横气焰逐渐消散,死亡的阴影悄然笼罩其上。曾以食人肉为战术的蔡军士兵,在这场雨中纷纷染上瘟疫,而孙儒也不幸中招。杨行密得知孙儒病倒的消息后,毫不犹豫地决定发动最后的进攻。
此时,田覠与安仁义出奇不意地展现了出色的作战能力,他们快速突破孙儒的防线,攻无不克,一路摧毁了孙儒五十多个营寨。命运弄人,孙儒此时病得虚弱,根本无法反抗。
最终,田覠亲手捉拿了孙儒。关于孙儒的被捕,史书中有两种说法:一是田覠亲自擒获了孙儒,二是孙儒因病重,部下失去信心,将其交给了杨行密。不管哪种说法,杨行密最终果断处决了孙儒,并将其首级送至京师。
曾经的枭雄,十国中的“大魔王”孙儒,最终在与杨行密的生死较量中败下阵来。而杨行密通过这一场以弱胜强的巧妙胜利,最终稳固了自己的地位,成为十国中最为强大的国君。
发布于:天津市道正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